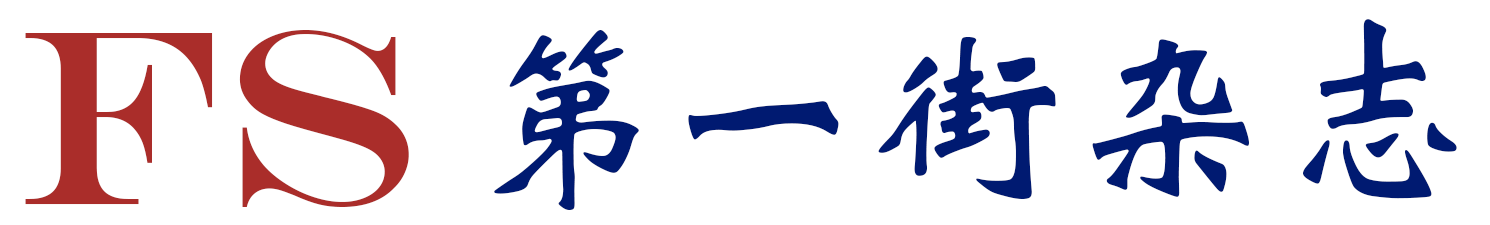大学时唯一一次奢侈是买了一台随身听。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女友的时代,校园的日子漫长而单调,节假日本地人回家享受天伦之乐,有亲友的也能享受到这份阳光雨露,外地孩子的节假日空荡而冷清,随身听是稀罕的消遣。
东财园校门外长长的小路两侧从地摊到报刊亭到多声道音响的音乐屋,有各种音像制品卖。很少买正版磁带,价格是一方面,好听的歌不多是另一方面。我们像分享烟一样分享磁带。宿舍里有一台便携式录音机,学校放英语听力那种,没有音质可言,却足以调剂单调的生活,播放我们打发寂寞的歌。今天回想大学生活还记得我们常常听的歌,熟悉的旋律让我想起睡在上铺的兄弟。
能够表达的情感才是快乐的情感,然而情感表达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今天微信可以秒发感情,那个时候无论同城还是异地都要写信。一封信往返,快的要两周,慢的一学期写两封信就要放假了。没到圣诞新年,学校的邮局信箱塞满了贺卡,有些塞在了外面,像圣诞树一样壮观。云中谁寄锦书来,是那个时代的喜悦。
1990年代中期,大约在大学二年级,校园附近可以买到一本叫《音乐天堂》的音乐杂志,中山大学出版的,以英文歌为主。以Jingle Bell作为英文歌启蒙的我们,听到这些歌犹如天籁,和平时听“花心”、“涛声依旧”一类的流行歌曲完全不是一个水准。曾经有一段,音乐天堂是我们宿舍必买的杂志。就像有烟和有酒的情谊,磁带也是大家分享着听的。Boyz II Men, Enya, Richard Marx, Michael Bolton, Simon & Garfunkel, Roxette, 这些若干年后才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歌手和乐队对我们还是陌生名字。音乐天堂后来因为版权问题停刊了,后来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终究无法突破法律的界限。音乐天堂昙花一现,是我那一代人对音乐抹不去的记忆,特别是前15期,很多旋律留在记忆深处。
同寝室的一个广东兄弟,每次要坐55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从广东到大连,舍不得买卧铺却舍得买很好的磁带。他每次总会带来TDK的透明磁带,里面是路过广州时付些费用从CD直接翻录的流行音乐。音质清澈悦耳,让我对CD和广州神往了好久。他带回来的磁带主要是粤语歌曲,谭校长、Beyond、张学友、梅艳芳、陈慧娴、张国荣。那时候听不懂粤语,同学会给我们用普通话解释,虽然有些粤语表达怪怪的,但也有些歌词直指人心,更重要都是用粤语唱出来的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即便是张国荣这样的跨界大家,也是粤语歌远远比国语歌更有味道。很多歌曲我一直喜欢到今天。
大学时学校有电影院,电影开始前有时候会放卡拉OK机,免费用。有一次有两个同学,貌似情侣,对唱了《相思风雨中》,也许情之所至,也许他们之间精神上的合拍很动人,我认为比原唱更好听。还有一次,一个兄弟用吉他对着一个女孩儿弹唱了周启生的《天长地久》,吉他声想起,现场迅速安静下来,歌声打动每个人的心。有时候用语言没法表达的话,就用音乐来表达。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天各一方,一起听歌一起唱歌的日子逐渐远去,但喜欢听歌听音乐的习惯却一直保留下来。工作后赶上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网络下载的歌曲多了,但还是喜欢到音像店里买CD来听,最喜欢大连友好广场一家音像店,有很多精品。每次到那里找一位熟悉多年的哥们叙旧后,都会到这家音像店停留片刻。
索尼MD 505 随身听是我在随身听后买的第二个音响设备。索尼是一家很伟大的公司,把一张CD放在那么小的盒子里,音质却丝毫无损,加上索尼717耳机,给人一个非常安静优美的音乐世界。后来出现MP3、音乐手机,只在便利性方面更胜一筹,音质却没法超越MD。这些年多次搬家,每次搬家都像着了一次火,少了很多东西,当年的老款随身听、索尼MD却一直随身带着,尽管我已经不用它听歌了。
在洛杉矶留学时,节日的一天去附近超市购物,推着购物车闲逛时超市播放了邓丽君的歌曲。对邓丽君的歌大多数耳熟能详,觉得很好听,没有其他感觉,但在异域文化里突然听到她的声音,一瞬间心弦被莫名地拨动,呆呆地听了很久。留学时听很多歌绝大多数都是中文歌,英文歌反倒听得很少。
苹果开辟了一个时代,让手机成为高端娱乐设备。网络时代听歌不必再到音像店去选CD,免费的、付费的网络音乐很方便。微博和微信经常有人分享音乐,一不小心就会遇到很惊艳的几首。某一天有网友在微博分享了阿南亮子的音乐Refrain,第一遍打开只是觉得好听。后来在去哈尔滨的高铁的路上再听这个音乐,轻快的节奏伴随着列车在辽阔的东北平原上飞驰,窗外的景色变化,黑管演奏的副歌悠扬婉转,人顿时被放空,心像自由的飞鸟,仿佛置身音乐的天堂。